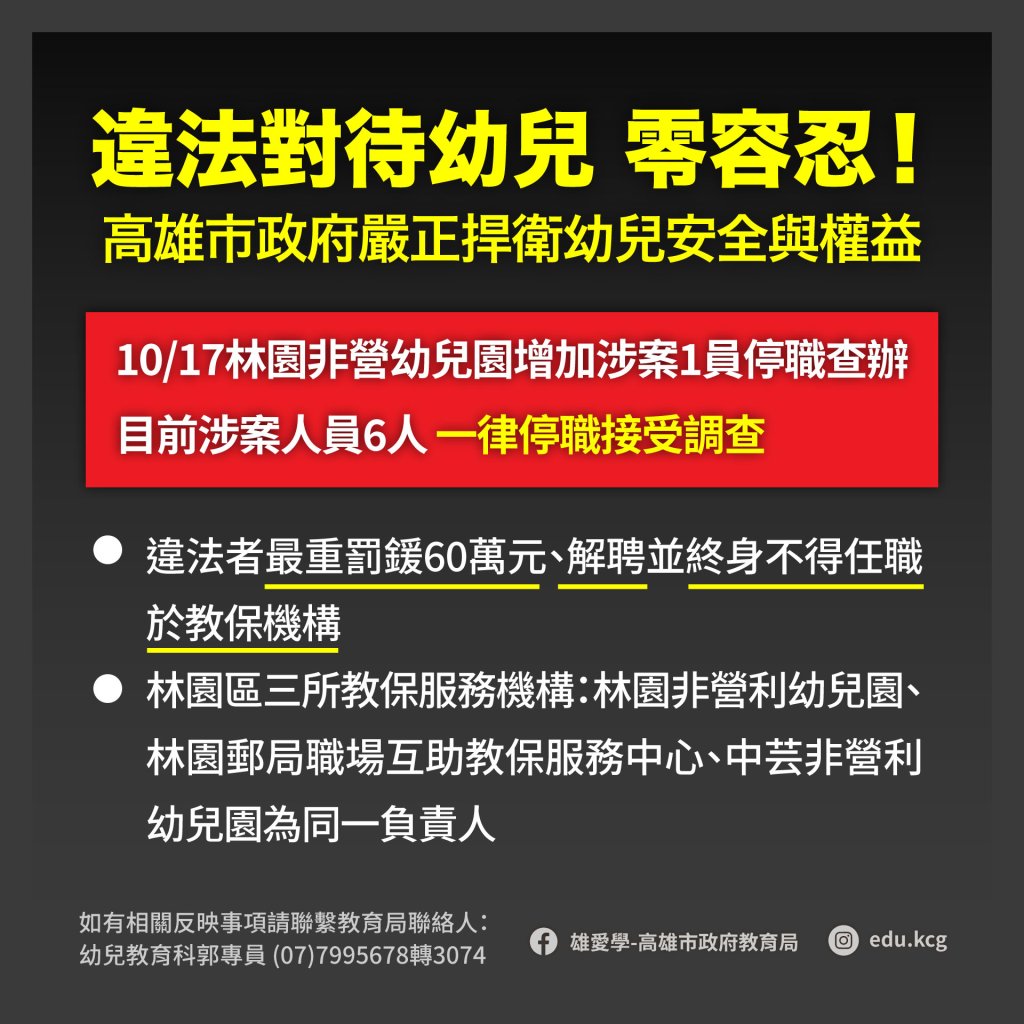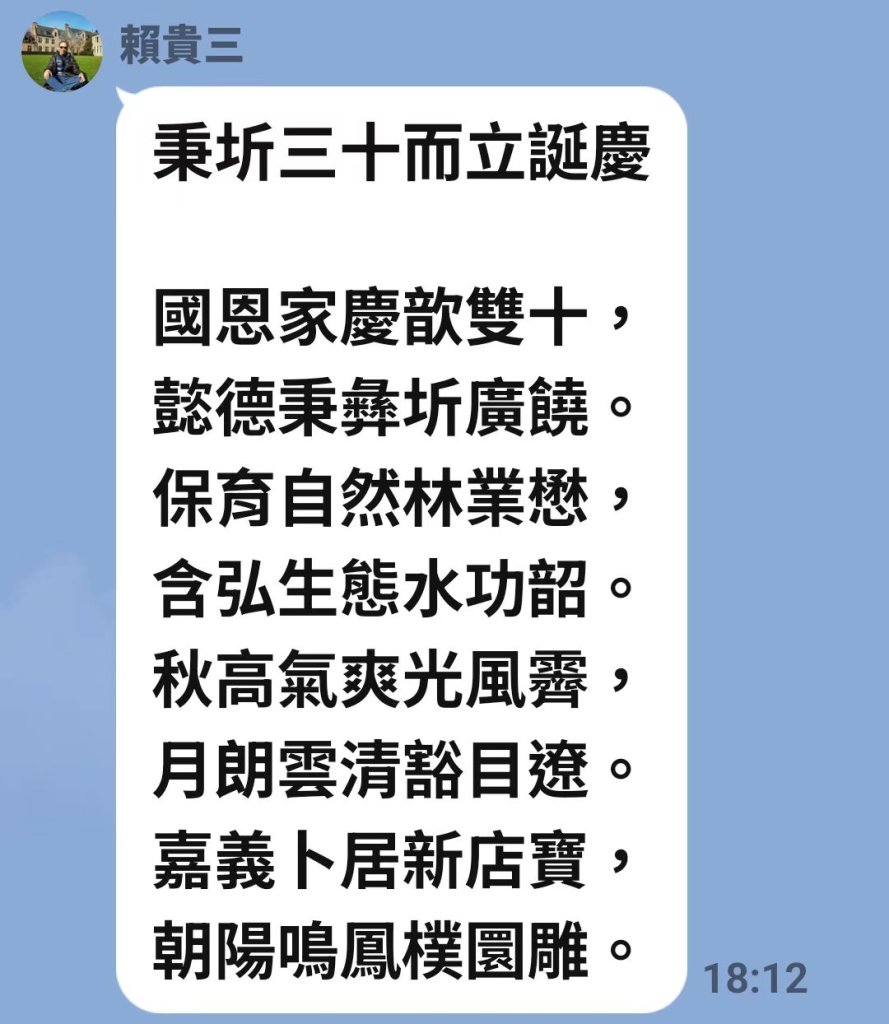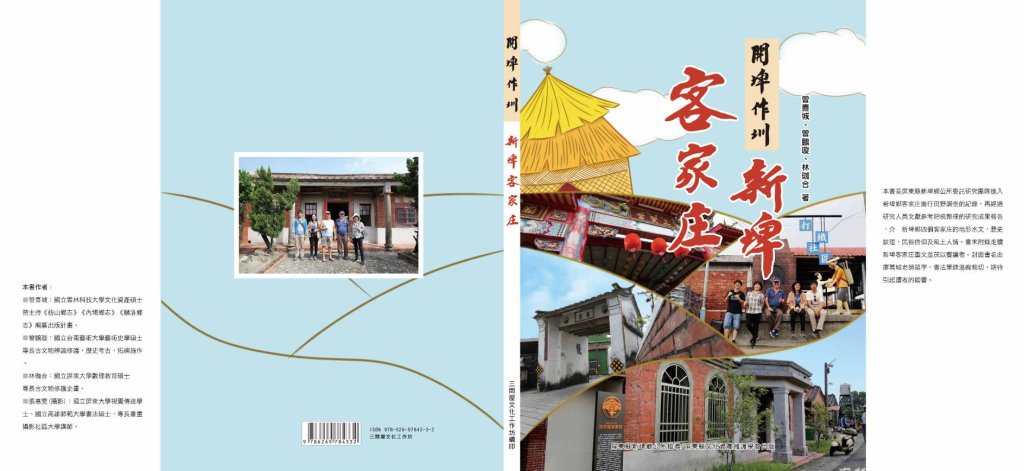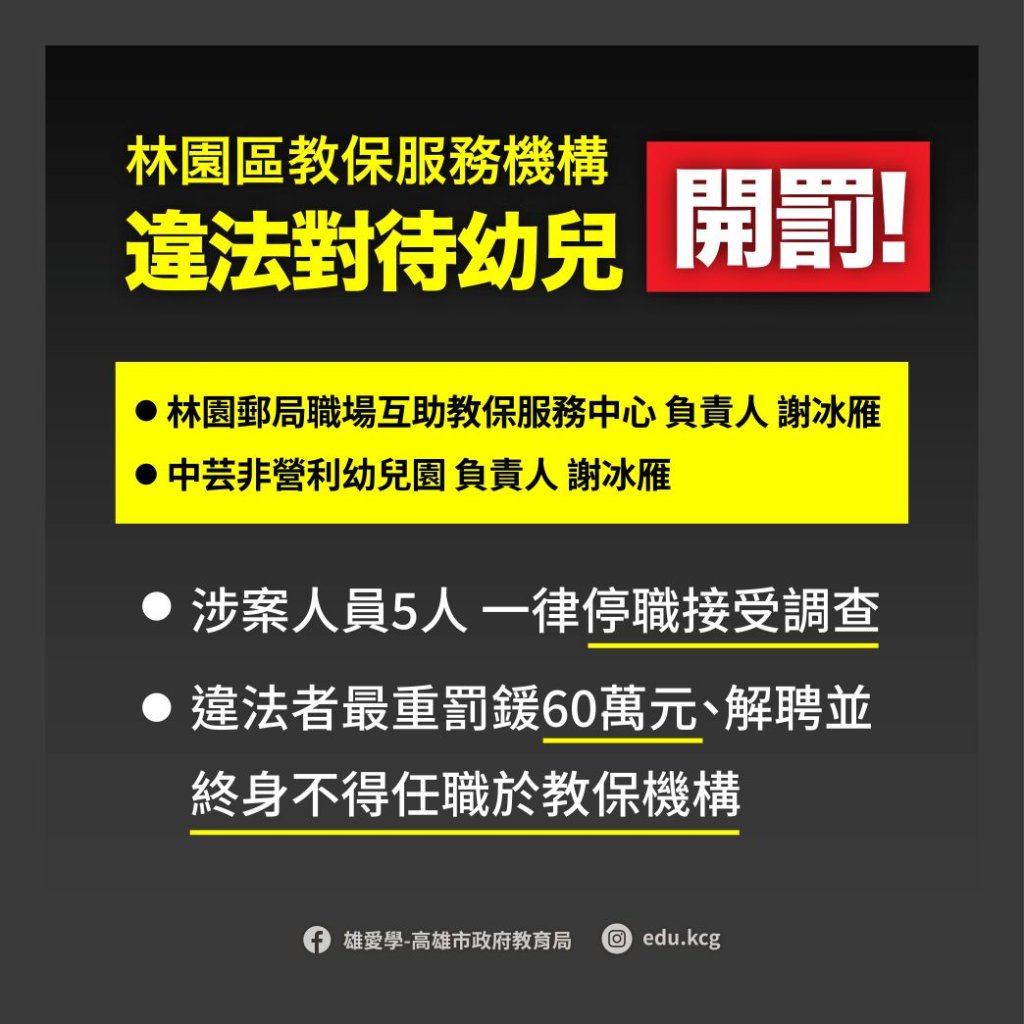引言:物件的再命名,感知的再打開
在當代創作語境中,「藝術」與「設計」的界線愈發模糊。兩者皆處理形式、材料與空間,也都與生活密切相關。然而,當我們面對一件由工業零件組成的雕塑、一段漂流木被立於展台、一組鏽蝕的金屬支架被重新編排為象徵結構時,我們不禁要問:這是設計?還是藝術?
本文以「藝術不是設計?」為主題,並透過空間(Space)、生活(Living)、感受(Feeling)來探討藝術與設計的根本差異,再以個人現成物作品為例,闡述藝術如何喚起時間、記憶與感知,使物件脫離設計的實用邏輯,進入詩性與哲思的場域。
一、Space:空間的轉化——從功能場域到感知場域
設計中的空間,主要以「使用」為核心——動線的流暢、視覺的平衡、功能的整合,皆指向一種目的性的實現。而藝術中的空間,則不以使用為前提,而是以「感知」為召喚。它不服務於效率,而是開啟存在的可能。
杜象(Marcel Duchamp)在1917年以《泉》(Fountain)顛覆了藝術的定義。他將一個小便斗置於展覽空間,使原本屬於衛生設施的物件,成為藝術語境中的挑釁與思辨。藝術已不再是製造物件,而是選擇物件。於是物件選擇正是空間語境的重構——物件不再是被使用的工具,而是被觀看、被詮釋的在。
.jpg)
首先在圖1中,一件金屬結構模型由實心方形底座、垂直金屬桿與錐形構件組成,實心若以設計邏輯觀看,它可能是火箭原型或機械支撐系統。然而在藝術語境中,它不再是功能的預演,而是象徵的生成。金屬的冷硬質地與垂直張力,召喚出工業時代的記憶;細線的延伸,如同感知的觸角,將觀者的視線引向空間之外。
這種空間的轉化,不僅是物件的重新命名,更是觀看方式的重構。觀者不再是使用者,而是存在的參與者。作品不再是設計的成果,而是語言的載體。海德格(Martin Heidegger)在《藝術作品的起源》中也指出,藝術作品能使存在顯現(aletheia),而非僅僅呈現形式。這些金屬結構,正是在空間中打開「本體」的顯現,使觀者進入一種非目的性的感知狀態。
在圖5中一件金屬雕塑,是以三腳架支撐整體結構,彎曲身形延伸出禪修意境,有如飛舞般蝴蝶綻放出飄逸的羽翼。這種有機形態與工業材質的結合,打破了空間的分類邏輯。它既非自然,也非機械,而是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詩性存在。觀者在空間中不再尋找功能,而是感受形態的流動與象徵的生成。
因此藝術中的空間,是一種「非使用性空間」—它不提供解決方案,而是提出感知的問題。它不設計功能,而是召喚存在。這種空間的轉化,讓我們重新思考物件與場域的關係,也為「藝術不是設計?」提供了不同的看法與思維。
二、Living:生活的重構——從使用性到存在性
設計最終的目的在於「改善生活」—它以人為中心,追求效率、舒適與美感的融合。無論是家具、工具或空間配置,設計總是指向一種目的性的完成:讓生活更好、更順、更美。然而,藝術並不以改善生活為目標,它關注的是生活的缺陷、矛盾與詩性。藝術不是提供解決方案,而是揭示生活的深層內涵。
尼采曾言:「我們擁有藝術,免得真理使我們滅亡。」這句話道出了藝術的存在理由——它不是逃避現實,而是對現實的轉化。藝術讓我們在混沌中看見秩序,在日常中看見神秘,在物件中看見生命。
其中圖3作品是一段傾斜而起的漂流木,木質紋理佈滿裂痕與風化痕跡,底座為圓形金屬圓盤,底盤散布凹陷的圓孔。彷彿訴說著海洋的記憶與自然的語言。若以設計觀點,它也許是廢棄物;但在藝術語境中,它卻成為記憶的載體、存在的象徵。觀者不再思考「它能做什麼」,而是感受「它曾經是什麼」。
另一件圖4作品則是門鎖扣環與類似繩索彎管組合。這些原本屬於安全與衛浴設備的物件,在手中被重新組裝,形成一種懸置的結構。扣環不再是開關器具,而是形象轉折的張力;彎管不只是跳躍的繩索,而是情感信仰的纏繞。
布爾迪厄(Pierre Bourdieu)指出,物件的價值不僅來自其功能,更來自其文化語境與象徵資本。在這些作品中,藝術家透過物件的再語境化,挑戰設計的功能邏輯,並揭示生活的多重層次。藝術的生活觀,不是追求完美,而是擁抱不完整。它讓我們看見裂痕、痕跡與時間的沉澱。
藝術的生活觀,不是追求完美,而是擁抱不完整。它讓我們看見裂痕、痕跡與時間的沉澱。它不提供答案,而是提出問題。它不改善生活,而是讓生活變得可感、可思、可詩。它讓我們在物件中看見存在,在日常中看見神秘,在使用之外看見感動。
三、Feeling:感受的召喚——從審美愉悅到存在震盪
設計的美感往往指向愉悅與舒適——視覺的平衡、材質的細膩、使用的順暢,皆為提升生活品質而服務。然而,藝術的感受性並不以愉悅為目的。它追求的是震盪,是存在的覺醒,是情感的召喚。藝術不一定「好看」,但它一定「讓人感覺」。
海德格在《藝術作品的起源》中指出,藝術作品能使存在顯現(aletheia),而非僅僅呈現形式。這種顯現,是一種感知的開啟,是一種存在的悸動。在以現有構件中,藝術家透過工業材料的重新建構,使觀者不再只是觀看形式,而是被材料的質地與時間性所觸動。

其中一件圖2作品是由螺帽、墊圈、金屬桿等零件組成,排列成一個簡化的「臉」的形象。這種組合既冷硬又親密——金屬的質地象徵著工業與距離,而對稱的構造卻喚起人類面孔的熟悉與情感。觀者在觀看時,既感受到物件的陌生性,也投射出自身的情感經驗。這種感受,不是設計所能提供的,它超越了功能與形式,進入一種存在本質的反思。
另一件圖6 作品是利用缺角結合成的金屬支架,以斜角排列方式放置平台上,一種不穩定的結構形成三角幾何的立體形式,訴說著物件的平凡過去與轉化的自主重生。這些支架原本屬於建築或工業用途,但在藝術語境中,它們成為記憶的載體、感知的媒介。觀者不再思考「它能支撐什麼」,而是感受「它曾經承載什麼」。這種感受,是對時間的凝視,是對物件的傾聽。
尼采也推崇藝術是生命的最高價值,而我們的生命便是自己最好的藝術品,因而我們應該從生命的觀點來看藝術。這些作品正是在生活中尋找形式,在冷硬中召喚情感,在無用中喚起感知。它們不再是設計的成果,而是感受的容器。它們不提供審美的愉悅,而是打開存在的裂縫。
因此,藝術的感受性,不在於「設計得好」,而在於「是否讓人停下來思考」。它不是為了讓人舒服,而是為了讓人不安。這種不安,是對存在的提問,是對物件的再詮釋,是對生活的重新理解。
結語:藝術的召喚,不是設計的延伸
「藝術不是設計?」這個問題的答案,並非否定設計的價值,而是在於肯定藝術的獨特性。設計以目的性為核心,追求功能、美感與效率;但藝術則以存在自主性為召喚,揭示空間的語境、生活的裂縫與感受的震盪。
本人作品創作亦致力多重藝術精神的體現,也期待他人能夠重新看見物件的本質、生活多樣的意義與感知的深層力量。在隨興的創作中,藝術不再是設計的附庸,而是存在的召喚者。
總之,藝術不是設計?—它不再強調於使用,而是注重於感知;它不追求目的,而是打開可能;它也不改善生活,而是讓生活變得可感、可思、可詩。
因此,在物件被大量生產、設計邏輯主導生活的時代,藝術提醒著我們:真正的創造,不在於功能的完成,而在於想像的開啟。現成物構成的藝術,正是在形塑空間、生命與感受價值中,重新認識自我存在的起點。